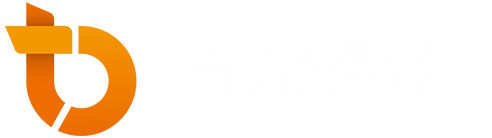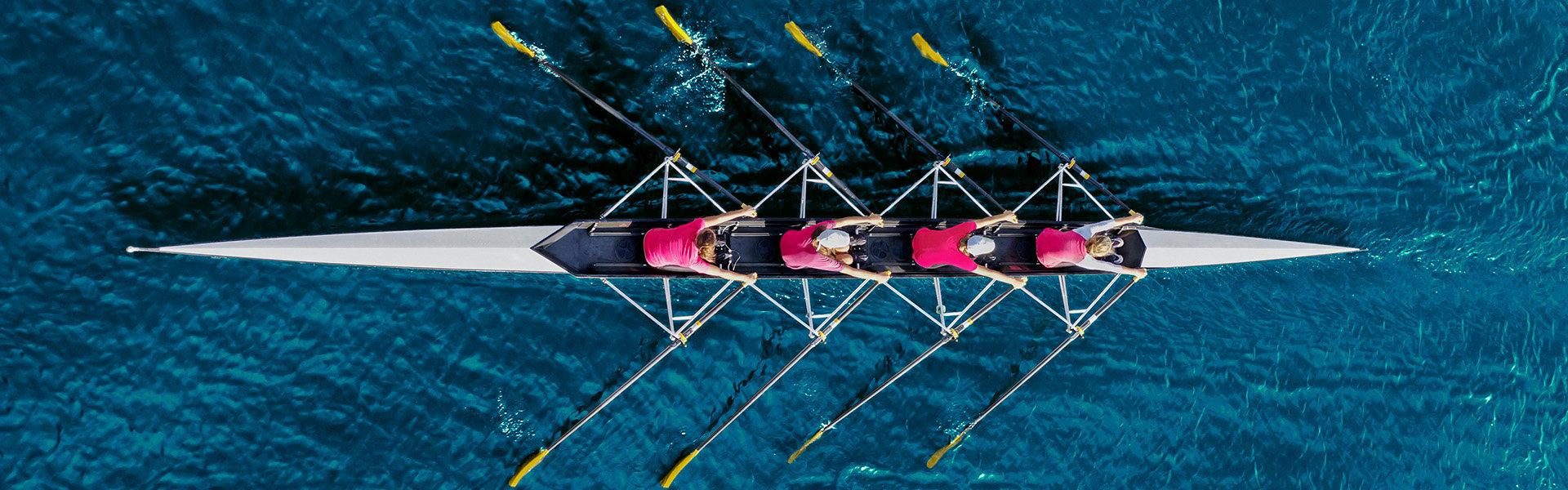为什么好电影越来越少?山海计划年度评委论坛“找答案” 山海训练营
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山海训练营正在广州中旅·阿那亚·九龙湖举行。在7月15日下午的山海计划年度评委论坛上,电影导演、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甘小二,知名策展人、选片人王庆锵,资深纪录片导演、奥斯卡学院会员周浩,知名摄影师董劲松,分享了对电影创作、市场的思考。时代变化与创作趋势,成为此次论坛关注的焦点。

参加此次年度评委论坛的都是经历了中国电影急速发展时期的中生代电影人。他们如何看待这些年与电影有关的变化?

甘小二最开始学财经,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电影理论研究生,2002年拍出了自己第一部电影长片《山清水秀》。如今,甘小二是华南师范大学电影创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他执导的传记电影《坪石先生》即将上映。他看到的是电影专业学生的变化:“拍电影需要好身体,现在学生体质没有以前好;而且学生的阅片量、阅读量非常有限,和我以前接触的学生不一样。”
王庆锵是记者出身,后来参与各大电影节选片工作,这件事一干就是三十年。谈及电影创作的变化,王庆锵直言:“现在的电影普遍没有上个世纪的好看,百看不厌的电影太少。”但是,他表示,中国电影的创作趋势向好,而且比日本、韩国都要好,“虽然市场环境很困难,但大家依然很有热情、活力,希望满满”。

周浩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做了几年记者后开始拍纪录片,《高三》《棉花》《大同》等作品广受赞誉。谈及纪录片创作的变化,周浩发现:“十年前,华语纪录片界每隔一两年会出现一部炸裂的片子。但现在,即便电影人基数庞大,但很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片子。而且纪录片创作需要对生活的历练和观察,但现在年纪大的纪录片导演越来越少。”
董劲松一开始学美术,后来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摄影,代表作有《南方车站的聚会》《地球最后的夜晚》《白日焰火》等。谈及电影创作环境的变化,董劲松说:“即便现在资本介入创作是大势所趋,但也需要有年轻导演做一些独立思考,进行自由表达,我期待与年轻导演合作。”

受到长、短视频冲击,投资环境变化的影响,电影会走向何方?面对不同的领域,四位电影人给出了展望。
甘小二面对的是电影教育问题。他在创作电影《坪石先生》时总会带几位学生深度参与各电影门类工作,希望他们从中寻找兴趣、方向,最终实现自由的创作,“中国电影市场被大制片厂、出品方、制片人等主导,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我始终认为,电影真正宝贵的表达,不是用钱换来的,并始终相信会有好电影人做出好电影”。
由于常年从事电影选片工作,王庆锵对电影观看媒介的变化极其敏感:“虽然目前看来,电影仍是大银幕艺术,大银幕会让观众被电影引导,但在小屏幕看电影的感觉也很奇妙,我大,它小,更容易看出细节问题。”他承认了大众观看电影习惯的改变,但不认为电影会因此消亡,“即便创作停止,前人创作的优秀电影都是宝贵财富,值得被观众看到,大家不必焦虑”。

目前,国内纪录片界出现了一大趋势:拍家庭、自己的片子多了,拍公共事件的片子少了。周浩表示认同,并给出解释:“纪录片应该对当下社会有关注度。可能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大家公共活动的缺乏有关,可能关注家人、自身比关注公共事件更容易。”不过,他也支持这种创作趋势:“我们不能指责纪录片导演关注自身不对,第一部片子拍家人、自己完全没有问题。”
谈及年轻电影人的机会,董劲松坦言,即便自己从以前十几万元预算的项目,拍到了现在一个多亿元预算的项目,依然会怀念独立创作的日子,也希望年轻电影人珍惜这段时光。不过,他提醒:“独立创作、制片的内容会很有意思,但要打磨好剧本。对于摄影师而言,即便我们是为导演服务的,但合作的前提是有好剧本。”
如今,短片成为青年创作者十分热衷的体裁,不少电影创投计划也将焦点放在短片扶持上。四位电影人对于该现象发表了看法。
甘小二直言,短片与长片在创作内核上并无差异,但指出当前短片普遍存在叙事仓促、表演薄弱的问题:“很多短片不能展开从容的叙事,表演也有点弱,是普遍现象。”他强调,短片的艺术完成度仍需以电影语言的基本规律为基石。

王庆锵以行业观察者视角指出中国短片生态的尴尬处境:“每年收到5000个短片作品,但我很少看。”他犀利批评许多创作者将短片视为妥协之举:“很多电影人做短片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而是因为没有钱做长片罢了。”他建议创作者还是要专注于90分钟至120分钟的长片创作:“如果你很想拍短片,可以把长片剧本的一场重要的戏拍出来。”
周浩以奥斯卡评委的经验指出纪录短片创作的困境:“让我选出一部最佳纪录短片,是很困难的事。”他也赞同王庆锵的观点:“如果能把短片作为长片的一个章节处理,是事半功倍的事。”周浩的个人创作则遵循随机性:“碰到好题材就拍了,没太考虑篇幅长短。”
董劲松的视角不同:“我更想看到青年导演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对自己和当下的思考,而不是技术表达。”

“在电影创作中,导演如何处理与观众的关系?是坚持自我表达,还是主动迎合市场?”提问环节,一位青年导演发出了灵魂拷问。
周浩反对刻意讨好观众,认为这样会丧失艺术独特性:“拍电影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参加电影节,也不是为了观众。我在生活的碎片中,寻找解构的可能性,最后碰巧遇到了喜欢我的观众。如果你一味讨好所谓大多数观众,肯定会失去你的创作特点,最后也没人会喜欢你。”尽管强调创作自由,周浩也承认,长期的媒体经验让他对观众喜好有一定直觉:“从内心来说,我不考虑市场,但我之前做记者的经验,让我本能知道观众喜好。这不是我刻意得来的。”
甘小二坦言,自己曾希望作品能被更多人喜爱,但现实往往相反。然而,一次观众的反馈让他重新思考创作的意义:“第一天,我曾经希望自己拍的东西能被人喜欢,但现场很多人不喜欢。第二天,有一个人鼓励我,哪怕你的片子只有一个观众,也够了。”他提出,创作自由度与资金来源密切相关:“如果用你自己的钱拍电影,你可以只为自己拍;如果你接受了别人的投资,你可以慎重一点拍。”